“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培养优秀的人才能够为学科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创新动力,而学科的发展又能够反哺人才培养,使其更加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而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科学精神至关重要。”
1月9日,在第十届医学家年会圆桌对话·院士篇,在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健康中国研究院院长梁万年的主持下,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希山、中国工程院院士丛斌、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福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围绕“科学精神如何指导人才培养与成长”展开深入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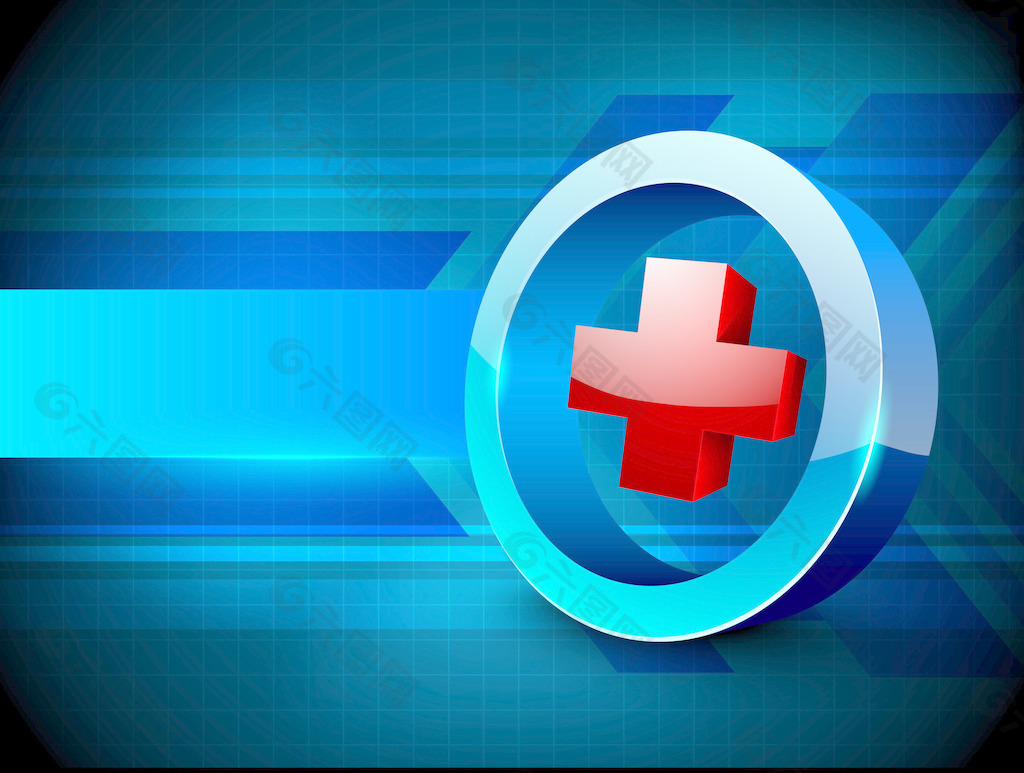
谈到科学精神,郝希山院士分享了天津医科大学原校长、天津市内分泌研究所首任所长朱宪彝教授防治碘缺乏病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朱宪彝教授发现病房里从承德来的“大脖子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地甲病)患者很多,就组织基础和临床多学科联合攻关,在承德进行了碘盐防治研究。在他的推动下,中国第一个专业机构——河北省甲状腺肿防治大队于50年代初成立。1956年,我国第一个内分泌科研规划也将地甲病列为重点,随后,地方甲状腺肿的防治列入了我国第一个农业发展纲要。
1959年,在朱宪彝教授的领导下,承德地区组织了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研究,证实了地方性克汀病(地克病)也是因缺碘造成的一种地方病,并开始了食盐加碘的防治观察,取得了明显的防治效果。最终,在朱宪彝教授和马泰教授的建议和努力下,促成了由原卫生部主持的我国第一个碘缺乏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中国-澳大利亚“控制中国碘缺乏病合作项目”,分别在天津、青海、黑龙江和贵州省开展了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临床和防治研究;建立了四个碘测定和新生儿甲低筛查的国家参照实验室;还在天津市内分泌研究所进行了碘缺乏病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使中国碘缺乏病的研究走出国门,与国际接轨,同时培养了一批中青年科技人才。
“这个案例,就是运用循证医学理念指导临床实践的代表——即从临床发现问题到实地调查、研究,最终再回归临床。”郝希山院士说,“也是在朱宪彝教授、金显宅教授等老一辈专家严谨求实的医学精神鼓舞下,为改善胃癌患者全胃切除后,无胃状态下严重的营养障碍,我通过反复动物实验和实验室研究,创立了功能性间置空肠代胃术这一创新术式治疗胃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科学家精神是家国情怀、是公而忘私、不计报酬、不计名利的刻苦攻关精神。科学文化则包含理性、求是、求实、遵规、诚信、开云注册平台合作、创新、纠错、向善等特质。”丛斌院士说,“本科期间,我学的是临床医学专业,后来又在西安医科大学攻读法医学硕士学位,期间,我深感‘法医是为司法审判服务的国家医学,不能光懂医不懂法’于是就白天上课做实验,晚上到另外的大学夜大学习法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后的1988年,丛斌院士以高于合格线多分的成绩顺利通过首次国家统一律师资格考试,并在此后做了15年兼职律师。“文理交叉学科的学习与锻炼,对我的成长、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医学科学创新过程中,我格外注重坚持问题导向,善于透过现象探寻问题的底层共性逻辑。”
丛斌院士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指出,科学研究要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然而,当前医学领域,人类认知的边界多由西方发达国家划定,我国在CNS期刊所发文章也多囿于这一边界,如何做到从0到1的创新,是广大医学科学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具体在生命科学领域,揭示生命本质规律是全球医学专家的急切任务。”丛斌院士表示,当下,学界普遍“青睐”结构生物学,尽管冷冻电镜(cryo-EM)技术带来了分辨率革命,让我们能够以原子级的高分辨率观察并描绘蛋白质结构;基于人工智能(AI)的AlphaFold等工具实现了对蛋白质结构的快速、精准的预测,但生命科学却不仅关乎解析人体微观结构,也必须探索结构之间的复杂关联关系,并且揭示网络化结构及其功能的时相性变化规律。后两个基本科学问题,很可能需借助大数据与AI赋能解决。上述三个基本科学问题的揭示是探究生命体分子互作的稳态维持机制,分子互作的疾病发病机制,分子互作的药效物质药理机制的科学基础。
“基于上述,在确定重大研发计划时,要拓宽思路、挖掘四大慢性疾病及其他慢病的共性致病机制、探寻其底层逻辑,从而研发共性干预措施。这需多学科交叉、系统深入联合攻关,并在此过程中培育创新型人才、彰显科学家精神。”丛斌院士说,“应在注重多学科交叉、善用AI的同时弘扬科学家精神,秉持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推动中国医学科研迈向世界前沿。”
从一名医学生成长为医学科学家,期间充满了挑战、艰苦,有成功救治患者后的喜悦,也有面对患者疾苦的无奈和深深的同情。如何才能历尽千帆,仍能不忘从医的初心,成为一名“好医生”?王福生院士表示,好医生涵盖了医德、医术多方面的要求。总体而言,就是要求医生始终以为患者解除病痛为目标,作为研究型临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好医生”标准可概括为 “三心、两艺、四能力”七个字。
“三心”是指对工作有责任心、对事业有进取心、对患者有同情心。王福生院士说,“‘三心’是医学的人文关怀的体现,更是医生医德的重要体现,只有拥有高尚的医德,才能成为一名好医生。”
“两艺”指看病的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手艺和创新的艺术。实践方面就是指 “治病救人”实际水平要高,这是医生的本职工作,医生要能对疑难危重与罕见病作出正确诊断,开云注册平台为患者制定正确治疗方案,力争解除患者病痛。王福生院士表示,“治病救人”也是医生不断研究、探索的目标,诊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医生应跟上时代的步伐,那么在理论上应掌握、了解、应用新技术、新成果,做到与时俱进。医院是创新的发源地,临床医生在日常工作中,应善于发现问题,并且把临床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开展科研创新探索。开云注册平台
“我们通常把既能做好科研,也能在临床会看病的医生叫做临床医学科学家。”王福生院士指出,好医生是科研创新的主力军,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临床研究,都要聚焦临床未解决的问题开展探索和创新,从而推动医学事业发展。他特别指出,在诸多医学前辈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医学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但很多优秀的科研文章都流向的国外杂志,导致我国在提升医学话语权方面面临一定困难。“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好研究、好论文可以发表在国内的英文期刊上,强化中国医学学术期刊在国际的话语权以及影响力。”
“四能力”分别为沟通能力、科研能力、管理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良好的沟通可有效减少医患矛盾的发生率,帮助医生更好的开展临床诊疗工作。”王福生院士表示,沟通不仅限于医患,也在于同事之间。让每一名医生都成为临床和科研的复合型人才较为困难,但作为研究型临床科室,应该大力培养擅长看病,同时又擅长做科研的医生,并通过协同创新,合力攻关,与其他临床医生一起共同发挥聪明才智,促进患者康复,推动医学发展。
“在现代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医依然具有相当的活力,主要原因在于其有确切疗效。”仝小林院士表示,在新冠疫情初期,疫苗和特效药都尚未问世,中医药在新冠患者救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后续的科研中,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曹彬教授牵头的散寒化湿颗粒与Paxlovid(后称“P药”)的头对头研究显示,散寒化湿颗粒在改善轻/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相关症状至持续临床恢复的时间,显著缩短患者咳嗽、咽痛、乏力的消失时间,其体温复常时间方面均优于P药,而P药在抗病毒效果上优于散寒化湿颗粒。
“该研究充分说明了中医与西医在思维模式上的差异——西医侧重于直接消灭病原体,而中医则致力于改善人体内环境,从而缓解疾病带来的种种症状。”仝小林院士强调,中医的三大核心思想——整体观、个体化、治未病——对现代医学有重要启示。他提到,当前整合医学理念,正是将过去零散的医学知识整理起来,其中,治未病与个体化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与中医部分诊疗理念不谋而合。
中医发展至今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仝小林表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过去中医看病以望闻问切的“黑箱”模式为主,而现代医学则为中医开启了“白箱”,让中医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以用药剂量为例,剂量是中药取得良好临床效果的关键,但随着历代度量衡的演变,经方的实际剂量成为“千古悬案”。而现代医学为验证剂量变化的对错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多项研究证实,在急危重症的治疗中,较现代小剂量药典,遵循汉代大剂量古方治疗效果可提升29%~50%,充分说明了“守正”的重要性与正确性。
仝小林院士指出,中西医结合已取得诸多成果,如青蒿素、活血化瘀、络病研究等,但在病与证结合方面仍有巨大探索空间。目前,中医的辨证与西医的疾病诊断尚未深度融合,证候与疾病规律、分期及阶段性指标关联性不足,致使中医在治疗时病、期、证分离。因此,他提出应在现代医学诊断基础上,依据现代医学分期和病理生理,运用中医思维总结各阶段核心病机,找到核心方和打靶药,构建中医既调态又打靶、态靶同调的新体系,弥补中医在打靶方面的短板,提高治疗精准度。


